
中国的世界遗产中六分之一的古建筑,沐鸣登录其背后的设计、建造与修缮都与“样式雷”有关。
_______________
被战火烧毁160余年之后,圆明园正以另一种形式被“看到”。
注视着它的人是王熙林,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器物修复研究所文物修复师。圆明园里的一栋戏楼正在他眼前,旁边还有一条买卖街、一座庙。这些景象,人们或许从清代圆明园《四十景图》里见过,但王熙林现在知道得更多。
他知道圆明园里的买卖街有房舍几间,设作何用,并能揭开房顶一探究竟;他能看到戏楼里有几根房梁、几架楼梯,甚至能推测出演员出入场的路线;被《四十景图》里的几棵树挡住的那座庙,他也第一次看到了全景。
眼前是一套100多年前的立体建筑模型——清圆明园同乐园建筑群“样式雷”烫样。这在当时,主要是为呈给皇帝审阅而制作。因为制作时需要熨烫纸板、秸秆、木头等材料,所以称为烫样。清皇家建筑工程,一般由样式房设计图纸、制作烫样,自清康熙年间至清末的200多年里,样式房的设计工作由雷式家族先后8代人主持,因此有了“样式雷”的誉称。据统计,中国的世界遗产中六分之一的古建筑,其背后的设计、建造与修缮都与“样式雷”有关。
清朝覆灭后,皇家建筑停造,“样式雷”家族逐渐败落。雷家后人为了维持生计,变卖了两万多件烫样和设计图档。王熙林眼前的这套烫样,由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于1930年左右收购,随后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又调拨给国博。目前,国博文保院正在对其进行修复和研究工作。
“这是现存样式雷烫样中规格最大的一套,也是圆明园建筑群中面积最大、级别最高的建筑群之一,是圆明园最全面、最真实的一份历史留存。”王熙林介绍,此建筑群自清雍正时期开始使用,至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这期间承担了清政府大量礼节、外交、宗室等相关活动,是一个功能性建筑群。
其中的中心建筑——同乐园大戏楼,是清代第一座三层大戏楼,与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楼、紫禁城中的畅音阁、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清音阁,并称“清代皇家园林四大戏楼”。据清人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记载,“演剧台深广约十丈,凡三层,神祇仙佛由上一层缒而下,鬼魅则自下一层穴而上”。戏台各层各有涵义,沐鸣注册地址表演时由机轴、天井、地井等设施辅助演员进出场。
“皇帝、皇后每年过生日都会来这儿听戏,戏演完了,赶上新春佳节还会去西侧的买卖街转转。皇帝和后妃也喜欢购物,他们会让太监在里面扮成商贩,中间还会有讨价还价,有人专门扮演小偷和衙役。戏楼东侧的永乐堂是一座佛教寺庙,在节日庆典之后供帝后礼佛用。”王熙林说。
这套烫样是35岁的王熙林从事修复工作以来,遇到的“最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它像一套微景观积木玩具,也让人想到售楼处的沙盘模型——但远远比这两者精细。烫样尺寸精确、比例严格,每栋建筑内外都贴着说明建筑尺寸和各处用途的纸签,连道路上的彩色鹅卵石都画了出来。
更精巧的是,建筑模型可以分层拆开,屋瓦、廊柱、门窗,甚至内部陈设的桌椅、床榻等小部件,都可以活动。王熙林惊讶地发现,在戏楼烫样内,负责演员出场升降的辘轳模型都是可以转动的,它不过一指节长。
由于珍贵易损,它只能和放置它的桌子一同移动——准确说来,那不是一张桌子。桌面是完全镂空的,放不了别的东西,是专为这套烫样而做的。其制作时间不可考,但王熙林曾看到桌底贴着一个签,隐隐约约写着:民国21年。
3年前,王熙林在库房看到这套烫样时,它就放在这张木桌上,上面封着一个玻璃罩,落灰严重。烫样一侧,有标签写着“清样式雷所做圆明园的模型”。他用一年时间搜集查阅样式雷烫样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但“相关研究很少……它不像玉石、陶瓷那样普遍”。直到去年把这套烫样搬进修复室,他也不知道这具体是哪一栋建筑的模型。随着清理工作的展开,王熙林团队根据模型上的匾额和贴签,比照档案资料,又在《四十景图》里找到了建筑的绘画,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
文物的基础信息有了,但还远远不到下手修复的时候,修复师需要看到更多。文保院藏品检测与分析研究所的修复师杨琴对这套烫样做了大量的科技分析与检测,包括屋顶结构、纸板材料、彩绘颜料和粘合剂等,一是记录其保存状态和病害信息,二是用试验的结果反过来比对验证档案文献的记录,尽可能探索出原本的传统工艺,以古修古。
多光谱摄影和X射线探伤帮助杨琴看到了更多细节,包括底稿的墨线、匠人的指纹和重描的字迹,不同的材料会显示出不同的发光特征。同乐堂戏楼临湖而建,模型底板上画出了湖边的淡黄色草植,但在紫外荧光的照射下,杨琴又看到了另一种颜色的草植。王熙林推测,这可能是为增加植被的画意和层次感而做的巧思,也可能是出于对上一个颜色不满意、要精益求精再画一层的用心。
文保院副院长成小林通过激光拉曼光谱仪看到,烫样上的颜料,既有传统的矿物石色颜料和植物水色颜料,如朱砂、花青,也有合成的颜料,如普鲁士蓝、巴黎绿。这与当时颜料使用的时代背景相吻合。1850年以后,西方人工合成的颜料因为成本低廉、色彩艳丽且附着力强,大量进入了中国市场,和传统颜料一起被广泛应用于古建彩画、绘画等行业中。
科学检测看到的细节越多,王熙林的修复操作就能越精细。扫灰清理之后,为了“建筑”的稳定性,他得先在不拆卸的前提下,给弯曲变形的“墙体”校形。“这是现在最难解决的问题。”王熙林说,“(毕竟)它已经弯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又是纸板做的,结构不稳定。”他的原则是以物理修复为主,不采用损害性的化学修复。
一道10厘米的“墙”,被“房梁”隔断成3节,每一节变形的曲度都不同。要想改变它,得先让“坚硬的墙壁”变得软和一点。王熙林拿着水壶,隔一层薄薄的宣纸喷水过去,等水汽慢慢洇软了纸板,才用三对尺寸合适的木块夹、垫、压、卡,把“墙壁”调成一条直线,轻轻用细绳绑着。薄些的“墙”需固定约7天,厚些的则需一个月。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时间,王熙林每天都要查看曲直的变化,不断调整力道和角度,以保证接下来的几十年它都不会再发生二次变形。
接下来,模型上的几百张贴签要压平、清理、复位,烫样上断裂的零部件也要重新粘合、补配。根据红外光谱检测,这套烫样的粘接剂采用的是动物胶——这和《材料账》中的记载相符。王熙林的修复也要用动物胶去做。但动物胶又细分为猪皮胶、驴皮胶、鱼胶等,还需要杨琴做更精细的检测。王熙林推测,使用鱼胶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自己先去菜市场买了鱼鳔,根据古法做了一小部分出来,正在做粘性和拉伸力的实验。他怕市面上买来的鱼胶有添加剂,对文物不好。
这像是与古人共同完成一件创作。王熙林偶尔能看到烫样上的指纹、设计修改的痕迹,或是一些意料之外的细节。比如,有些“房顶”底部的用纸,看上去是画押的印章。他猜想,可能是匠人做的时候着急,把这些纸都拿来当废纸用了进去。这是工艺之外,人的痕迹。
目前,王熙林团队的修复工作只是围绕中心戏楼展开。接下来,还有伴戏楼、永利堂、买卖街和其他房舍的修复任务。整个建筑群要完成修复,预计要到明年。同时,他还在探索更高难度的工艺还原,试图用消失百余年的雷氏家族的制作方法做出一个复制件,“至少后年中心戏楼要做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王熙林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通过实验比对,发现用石板和压缩机可以替代熨斗完成“烫”的这一步,并且纸板成品更不容易变形。如果当时也有这样的技术,烫样或许会换个名字?王熙林也无法猜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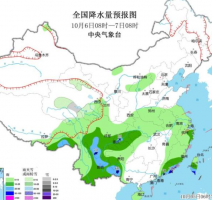


影片点评